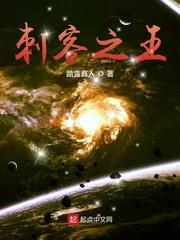52格格党>她不坠落 > 第 7 章 向她攀升(第1页)
第 7 章 向她攀升(第1页)
王醒衍很少做梦。
离家之后第一个闯进睡眠的梦境,是几年前的寻常清早,养父带他外出晨跑。少年的身体年轻单薄,但脊梁笔挺,步伐扎实有力。养父渐渐有些跟不上他的步速,终于将粗厚温热的手掌撂在他肩头,沉声要他把名字里的“言”字让给新降生的弟弟。
王醒衍奔跑的脚步慢慢停了,仿佛胸腔填满冻土,沉甸甸地往下跌,让一颗心也逐渐冷却。神情却仍是一径温顺,含着眼帘点头说好。
他的名字只做这唯一一个音节的改动,就陡然变得波折拗口,像咬字时呛了一块布满突角的冷硬石头。
那次他梦醒时分只觉一阵恍惚,躲在温暖舒适的被子里不愿睁开眼,朦朦胧胧地以为自己还能够缩回曾经被叫作冬冬的童年里去。
还有一次梦到他在家中受到冷落的那段光景。养父母的亲生儿子出生后,王醒衍的日子变得不太好过。从“言”字开始,他被迫让出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,直至退无可退,终于将他的家也拱手于人。
而梦到谈芜是完全不同的感受。上回在花园里他并没有看到谈芜的样子,只知道她嗓音沙甜,不是清脆爽朗的类型,倒像瓜果过熟的红瓤。她发出声音的两片嘴唇也非常漂亮,凉润的淡粉色泽。他频繁梦到这两页唇瓣翕动开合,对他说着什么话。
王醒衍不明白为什么女孩子甘美的嘴唇会出现在自己的梦中,也不明白这究竟象征着怎样一种意味。
在第三次梦到谈芜之后,王醒衍终于决定去找她。
他只知道自己必须要道一声谢。
再次按响门铃,心境已经不同于以往。来应门的换成了一个年轻脸孔,礼貌问他有什么事。
王醒衍说:“晚上好。打扰了,我找谈小姐。”
年轻的阿姨开门将人迎进来,仔细端详他挺秀的五官,面上顷刻浮了笑:“你是小满的朋友吧?请跟我来。”
静谧的花园里,此刻夜重灯轻。从别墅窗口隐约传来微光扑朔,照着庭院中心凝停的喷泉,偶有晚风慢拂,挑动着水意涟涟勾荡。走进室内才发觉,这黯淡的光线原来是星星点点的烛火,灯影稀薄地映在洁白墙壁上,也如水纹般摇晃。
阿姨领他换了拖鞋:“你是唯一一个来给她庆生的。你们关系很好吧?小满在这边几个月了,一直没什么朋友……”
原来这天是她的生日。
王醒衍低头看着自己一双修长的手。白皙皮色下,血管本来是青蓝的,被冻成极浅淡的紫色。指节横布细微伤痕,是工作中难免的磕碰所致。不过异常清洁,今天换下工服匆忙来找她,并没有忘记要仔细洗净双手。
可手心空空如也,他没有什么能够送给她。
别墅没有开灯,只点着不少蜡烛,满室都捂上一片温暖的融黄色。她穿吊带裙,正背对着门口,肌肤下方透出纤薄美好的肩胛形状。听到脚步声,谈芜回过头,好似一眼就认出了他:
“啊,是你呀。我好像还没
有要送去打理的衣服。”
王醒衍也终于看清了她小猫一样的眼睛、有着翘鼻尖和尖圆下巴的脸。
他试图稳定心神,还是未免从嘴唇紧张到脊梁,膝盖都在往后压,但是声音依旧轻轻淡淡,跟眼神一起穿过昏黄光线:
“生日快乐。对不起,我没能准备礼物。”
王醒衍并没有拿他的不知情作为理由,更不会徒找借口,只是向她承认错误。谈芜听清他的话,一时露出讶异的神色,似乎从没想过从这个还算一半陌生的少年手里收到礼物,想了想,先告诉他上次的事:“小张阿姨已经被辞退了。我告诉过洗衣店的老板,是我非要你弹钢琴的。”
“嗯。我这次来,就是想说声谢谢。”王醒衍心念微动,目光转向圆厅里那架白色施坦威钢琴,稍作沉吟后说,“如果你喜欢的话,我还可以弹给你听。”
他送给谈芜的乐章,叫作《圣婴之吻》。几乎未经拣选,是最先浮现在脑海的答案。坐上琴凳的一刹那间,已本能地脖颈轻仰,呈一种虔诚而膜拜的姿态。
对于这一首梅西安的经典曲目,王醒衍演奏得相当纯熟,对音程与和弦得心应手。谈芜看到他抬首却垂目,疏朗的眉宇之间,游过烛色熔金的浮光。琴声渐渐厚密,仿佛产生某种隐秘的感召,谈芜忽然发觉,上回这个样貌优美的男孩子技法还很生疏,他真正的琴技其实远远超乎了她的预料。
一曲终结,王醒衍指尖战栗,一半是如今做惯体力活的两手已经很难支撑这样的弹奏强度,另一半则是懊恼自己中途错了几个音。
他几乎是本能地觉得,呈现在她眼前的,应该是最完美的一切。
而谈芜却说:“今年爷爷买了一辆车,为我订制的车型和颜色,但是要等我明年回到美国才能看到。妈妈也准备了礼物给我,她一直都知道我喜欢什么样式的珠宝。这些礼物用钱就可以买到,可钱是最无足轻重的东西。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时间,这也是他们唯一不能分给我的东西。哦,还有一样——他们说只要我想,他们可以送来天上的星星。”
她顿了顿,轻轻摇头,“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,没有人可以为我摘下一颗星星。”
话到这处,谈芜好像一下恍然,眼睫跳跃似地眨动了几下:
“我又讲了太多无关紧要的,是不是?”她非常坦率,好像对自己意识游移的小毛病颇为理直气壮。王醒衍不由轻笑起来。唇角的弧度拉开,面上的肌肤紧跟着扯起丝丝涩意,他就在这时忽而意识到,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露出笑容了。
谈芜却没有注意到他的心神变化,一本正经地对他道谢:“不管怎么说,我都很喜欢。你送了我一首钢琴曲,而不是一架钢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