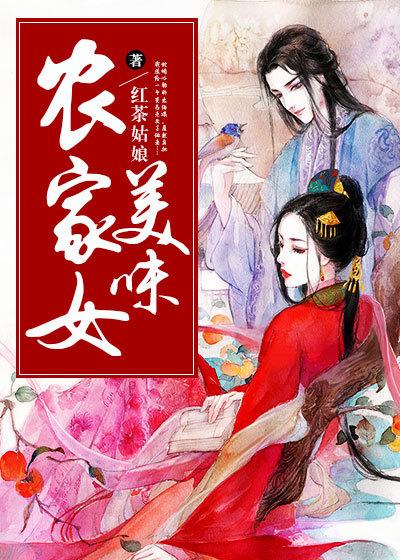52格格党>重生:黑莲花医妃杀疯了 > 第四百二十六章 爱屋及乌(第2页)
第四百二十六章 爱屋及乌(第2页)
“既是如此,我便……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慕锦月见楚凌夜如此说,的确是不好再过推脱,便答应了下来。
“但我却有一个要求。”慕锦月话音一转,又正色道。
“稍后阿夜定要陪我去向父亲与兄长请安赔罪。”
楚凌夜听闻慕锦月所言,眉头微微蹙了蹙便要开口,慕锦月却不待他开口便又郑重地道:“阿夜,今日,我定是要前去拜见父亲与兄长的。”
“我明白,父亲不喜人打扰,日后每日的请安……自可以免去,但我作为新妇入了镇南侯府,今日这进门后头一日的请安,却怎么也不能不去。”
“否则……若是日后被他人知晓此事,却不知要如何议论我这新妇不懂规矩,才刚入门便如此恃宠而骄、目无尊长。”
楚凌夜原本满不在意,听闻了慕锦月此言,倒是面色瞬时凝重了起来。
他只想着让慕锦月之后于镇南侯府的日子如何乐得自在,倒是的确没有想到此层。
楚凌夜向来便不在意他人闲言碎语,但若经受这闲言碎语的是慕锦月,则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
他如何舍得让他人妄议半句慕锦月的不是。
“好,稍后用过了早膳,我便陪月儿前去向父亲与兄长问安便是。”楚凌夜微微正色道。
于是待
楚凌夜与慕锦月一同用过了早膳之后,便又一同前去了楚侯与楚凌远的院子,分别向楚侯与楚凌远问安。
楚侯与楚凌远的反应如出一辙,均是对慕锦月极为和善,在她因今日迟来问安心下愧疚之时,对她百般安慰不说,还一再强调在镇南侯府中并无那般繁琐的规矩,日后大可随心而为、不必拘束,更不必在意他人所言。
即便楚凌远此刻身子虚弱、已是不便于行,但仍是极为认真地叮嘱楚凌夜定要好生对待于她,万不可让她受委屈,还言笑晏晏地对慕锦月保证,说若她受了楚凌夜的欺负,大可以随时向他告状,他定不会轻饶了楚凌夜。
兴许是爱屋及乌,慕锦月能够极为真切地感受到,楚侯与楚凌远言行之间是真的将她当做了自家人。
于是在她与楚凌夜告别了楚凌远、自他的院子中出来后,慕锦月满心暖意,心内无限感慨。
前世自打从她意识到赵氏对她的冷漠时起,直到身死于日月阁地牢之中,在威远侯府中生活的这十余年,她从未有一日真的随心而为、毫无顾忌地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虽说慕候极为宠爱她,但却久不在京中,于是她逐渐便极善于察言观色,总是小心地看着赵氏与慕秋霜的脸色过活,处处小心谨慎、克己守礼,唯恐惹得赵氏愈加不喜于她。
虽说重生之后她便再也未曾那般凡事委屈自己、忍气吞声,但因这些年
来拘束惯了,且又知道了她的身世,明白这威远侯府并非是她的家,她便更是有了寄人篱下之感,所以也从未有一日真的全然自由随心。
人人均说,待女子出嫁之后到了夫家,孝敬公婆、顺从夫君,定要万般恭谨,不可有丝毫闪失,否则便会惹得夫家嫌恶,日后定会不得安生。却不想如今她嫁入了这镇南侯府不过一日,丝毫未受到半点为难不说,还竟感受到了一丝真正的家的温暖。
她便像是漂泊无依了十余年的一艘游船,不知来处、亦不知去途,却在今日终于有了可以泊停之地,让她顿觉无比安心。
对于日后在镇南侯府中的生活,此刻慕锦月已是毫无先前的忐忑之意,而是充满了期待与憧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