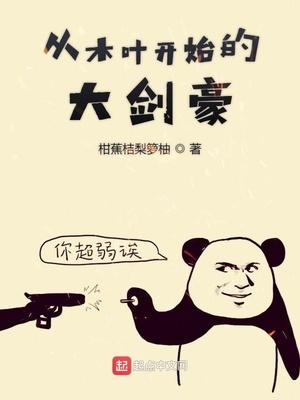52格格党>与君分杯水 > 第139章(第1页)
第139章(第1页)
旁边站着一名幕僚是他心腹,见状伸手取过来一读。松了一口气之余,只能微微苦笑。
信是戡明写来,先作辞,然而言道下月将妹子嫁于钶笕,力邀容湛前去见礼,言词之间隐见得色。末了才提到容瑄。
戡明那里有什么妹子,这婚事无端的就有些古怪。钶笕当日在堂上众臣面前揽下容瑄之事,此时纵然是后悔了。寻着如此借口,未免也欺人。
但好在容瑄平安,也是一桩好事。
幕僚默默收了信纸,也不多提。想了想对容湛道:“王爷,既然九王爷无事,是否劝皇上撤军。”
那日容卓同刘敬亭赶至画舫。瞧着一地狼籍,几人尸首横死当场,容卓顿觉得整颗心都揪起来,一时痛得几乎要喘不过气。他通身冰凉肝胆欲裂,悲怒交加之下,喉间一口腥甜再也压不住,当场就吐出一口血来,将众人惊得手忙脚乱。
他却不管不顾,脸色静得吓人,推来上前要来搀扶的侍卫,疯了似的满船找了一遍,见尸首中并无容瑄,这才略略镇定些。
刘敬亭一见眼前情景,也变了脸色,他倒不如容卓那般关心则乱,细看见众人都是一刀至命,挣扎的痕迹甚少,又唯独少了刘广一人。此处又无外人得知,情知其中可能有误。但事到如今反而百口莫辩,就是争辩自己对此也是毫不知情,对皇帝来说不过是火上浇油,未必听得进去。在皇帝失神众人惊慌当口,借乱走脱。
皇帝正在怒气头上,失了容瑄这枚棋子,他毕竟还不想就此与朝廷冲突,连夜调集兵马朝南郡撤去。一面派出探子寻找刘广容瑄下落。他视刘广为亲信,如今却在此人身上吃了亏,如何不恨之如骨,寻回此人一方面可向皇上有个交代,另一方面自要好好算算这笔账。
容卓却那里肯放他走脱,发了狂似的众人也拦不住,待容湛得到消息,他已经调集人手一路急追下去。
好在随行的人中有两名沉稳将领,容湛只挂心容瑄,对这贼人只恨不能生噬其肉,对皇上此举反而不如何在意。
“刘敬亭早有所准备,一路顺风顺水,皇上未必追得上,等进了南郡境内便不能再拿他如何。”容湛闻言皱眉道。“只须暗中让随行副将知道,实在追不上之时,再劝他回来。”
容帝离宫出逃,掀起这么大乱子,并非平安无事的找到容瑄,这事就能够从此揭过。今后睁只眼闭只眼容得下他如愿以偿。
钶笕那头又生出这诸般事情。虽不至于没有此人就如何,可这般出尔反尔的举动,无疑就让人猜想是生出嫌弃之念,堵得他胸中尽是一团恶气。这般一团乱麻的局面,皆因容卓而起。此时此刻,容湛更不想见到他,
何况就算容卓知晓,一来一回也是一两日后。索性由得他迟两日,这边先将这事了结。好歹是自己从小看到大的弟弟,自己再怎么管教可以,却容不下让外人来侮没。
因此留下一部分人手接应容卓,带着其余的人手匆匆启程离开徐塘。
——————
戡明打得好一手如意算盘,却未能如愿。
第二日一行人才投了店没多久,钶笕就急匆匆找上门来。
戡明见他,初是极高兴的。转念一想不由得悖然,他又是如何找到此处的?左右看了看,几名随从只顾闷头吃饭,都不曾抬眼看他。一时也分辨不出是谁向钶笕走漏的消息。
戡明只得恨恨作罢,回过头来斜眼瞧着戡明,哼了一声,漫不经心道:“你来做什么?”
若是钶笕知趣,先体贴问候他几句,倒也就罢了。偏偏钶笕匆匆进来,往周围扫了一圈,直直走到戡明面前,急急就问道:“容瑄呢?”
戡明大怒,只觉心中满腔邪火无处可泄,将酒碗朝桌上重重一拍:“我那知道他在那里、他又是你的什么人。”顿了顿瞧着他道:“你找他做什么?”
钶笕怔了一怔,这才听出他话里些微酸味,微微苦笑起来:“你不要闹了。我真有要紧事。”
“什么要紧事?”戡明紧追不舍。一转念道:“我已经同他说了你完婚的事,免得你开不了口。”
钶笕脸色有些黯淡。完婚之事虽非他自愿,但那血肉并不是做假。他即不能置戡明于不顾。对容瑄又委实难于割舍,纵然心知自己再不可能迎他至离原,又如何能亲自对他说出这番话。是以近情情怯,犹豫不决之下,才让戡明寻着机会抢在前头。
戡明牢牢盯着他,目光灼灼。钶笕只得道:“和这事无关。”
“不是这事是什么事?”
钶笕一窒,左右看了看,觉得不妥,只得低声道:“总是极要紧的……”
这家客店甚小,戡明索性就使银子全包下来。虽然他银子给得痛快,到底一行人形貌高大粗犷,小二店家都见过些世面,却还是心里有些害怕。给几人打点好饭食热水。不闻叫唤也不到眼前伺候。
四下桌子散坐着的,都是戡明带来的随从亲信。此时各自埋头吃喝,也不朝两人多瞧。
戡明皱眉:“这都是自己人,有什么不能说的?”
钶笕四下一看,依然沉吟着不肯多说,只追问容瑄下落。这一次他倒多了几分心眼,知道戡明吃软不吃硬的性子。温声细语地好言相问。
戡明这才心里舒坦一些。见钶笕神色间急切之情难掩,反而严肃不少。掂量了一阵,不情不愿的指着楼上:“他在上面。”
“我们上去说。”钶笕道,见他不动,也没有多想,伸手就拉住他住楼上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