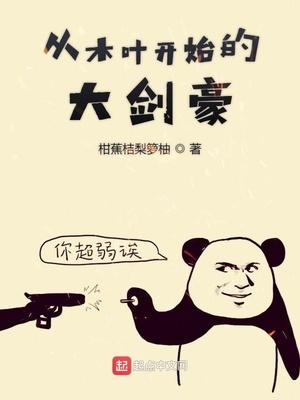52格格党>恰如天上月 > 第324章(第1页)
第324章(第1页)
李勖心里曾经闪过一个念头,有朝一日,若是他消灭了兵锋所及的一切敌人,君临天下,他或许并不会感到多少快慰,反倒会有些失落。
像他这样的人,说“仁爱”实在是太过抬举。
老天也看不过去,在他如痴如狂时收走了他的灵奴。他的儿子一去不复回,如同人生不能再少,流水不能西归。
李勖想,原来这就是人命。
西方的火烧云在视野中模糊成一片黯淡的红光,千军万马和王图霸业都烟消云散,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灵奴,那是他和韶音的儿子,一想到这里,李勖的心就碎了。他英雄气短,儿女情长,沉湎于悲痛不能自拔,在尸堆上昏沉睡去。
谢候唤不醒他,只好将他背到身上,一步一步往回挪。卢镝有些不知所措,犹豫问道:“……屠,还是不屠?”
“屠个屁!”谢候吃力地将李勖往身上耸了耸,喘着粗气道:“这个军令不能执行,等到主公醒了,你们只管推到我身上,一切后果由我一力承担!”
李勖倒下去之前给他们下达了最后一道军令:此战不受降,屠尽黄发鲜卑儿,包括俘虏的和洛阳城中的,一个不留。
这个军令打破了李军一贯的传统,李军从不杀降卒,更不会屠城。将领们都知道主公是受了莫大的刺激,他们不愿意执行这样的命令,也不敢抗命,一听谢候这么说,都松了一口气。
孟晖看着偌大一座洛阳城,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,有些不可置信地自言自语道:“洛阳啊洛阳,就这么打下来了?”
“可不是,就这么打下来了。”卢镝在一旁接话,踮起脚回望潼关方向,也有些不可思议地感叹:“两天一夜啊,光是急行军也能将脚累残了,竟然就这么杀了两天一夜。”
“慕容康那小子不孬,可惜世上只能有一个真龙天子,他算是遇上了克星!你们猜他这会在干什么?我猜,他一定想不明白,明明是一场胜券在握的仗,怎么就打输了,还输得这么惨!”
“别说他想不明白,我也想不明白,咱们怎么就赢了,你明白吗?”
“不明白,反正就是赢了!”
“话说回来,咱们好像还没输过,是吧?”
“别、别高兴得太早,慕容康放、放弃洛阳,退守邺城,这步棋没、没错,小矮马和徐——霄云拖住了魏军,咱们还、还是两线开、开战,形式不容乐、乐观吶!”
……
将领们暂时松弛下来,在下一场战役来临之前,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,谢候的心却仍悬着,李勖人高马大,昏得不省人事,背在身上死沉死沉。
谢候并不担心他的身体,军医方才已经检查过,李勖脉息稳健,除了表面划伤几处油皮,别的什么伤都没有,还不如谢候挂彩挂得多。
命大是成为名将的首要条件,李勖不光命大,还有一具强壮得令人嫉妒的身体,精神崩溃了,□□还能再克几座洛阳。他现在只是因为力气耗尽又极度悲伤而陷入了短暂的昏迷,用不了多久就会醒来。
谢候能趁他昏迷时阻止一个疯狂的军令,若是他醒来继续发疯,谢候也没把握能拦住他。
“越明”,谢候唤来孟晖,低声道:“烦请修书一封,寄给你姑父,主公这样下去不行。”
孟晖的姑父就是温衡,谢候不得不向温先生搬救兵,既然姐夫回不去,那就只好教阿姐过来。
……
关中的粮食缓解了江左的饥荒,死亡的人数在逐日减少,大晋像是个大病初愈之人,缓慢地汲取营养,缓慢地恢复活力。
万象复苏之中,江陵城里却多出一个心碎的母亲,与韶音不同的是,莹琼的心碎不能为外人道,这无疑更为煎熬,几乎将她逼疯。
韶音上次见她时,以为她的精神有些不大正常,其实她正常得很,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,只不过是韶音没有当真而已。
莹琼恨韶音,她希望韶音生不如死,这与王微之有一点关系,但关系不算太大。
莹琼姓庾,庾氏女郎与所有世家女郎一样,自幼便将一种观念根植于心:既享家族庇佑,自当一生为家族效命。
谢韶音毁了士族,毁了庾氏,庾莹琼就要以牙还牙,毁了她。
谢太傅说的没错,莹琼是个心藏锦绣之人,她不是个只会跟在王微之屁股后头争风吃醋的草包。
她一早就想的很明白,令自己念念不忘的不是王微之,而是以王微之为光耀中心的那个如梦似幻的少女时代。可是如今,如玉的郎君,不绝的丝竹,秦淮河的软艳,朱雀桥的晚霞,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锦绣年代,都与她曾经丰盈的香腮一样,一去不复返了。
庾莹琼恨死了谢韶音,儿子失踪的这些天,她在洁白的帛布上反复写着“生不如死”这四个字,一想到谢韶音也和她一样生不如死,她就痛快了,全凭着这股痛快劲,她才能茍活下来。
门锁从外边动了几下,庾护走了进来,回头命令把守的侍卫都下去。
“找到了吗,阿猷找到了吗?”莹琼问他,枯瘦的手像吸血的蚂蝗,牢牢地吸附在庾护的胳膊上。庾护被她抓得生疼却没有呼痛,眼神闪烁了一下,“阿妹,坐下说。”
他挣脱开莹琼的手,将手里的食盒撂在案上,从里面拎出一壶温酒。
“没找到,是不是?”莹琼才热起来一点的心又凉了,尖声道:“那你回来干什么?你去找啊!”她将庾护往外推,歇斯底里地叫嚷,“你去找,继续找!”
“莹琼!”庾护两眼通红,双手攥住她的肩膀,压低了声音道:“如果能找到,早就已经找到了,那个时候到处都是灾民,阿猷他……他一定是活不成了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