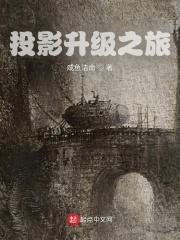52格格党>鳏夫十六年 > 4050(第4页)
4050(第4页)
谁让薄大小姐素来是这晋国王公贵族都争相捧着的姑娘,父兄手握重兵,姑母是太后,表兄是国君,且杨郡百年世家屹立不倒,门客遍布天下,薄家人的头发丝掉了一根,朝野怕都要震一震。
可怜那钧武侯年过五十还得了这个女儿,爱得跟眼珠子似的,几个哥哥也都是把这小妹妹捧在掌心里,养成她一副娇纵跋扈的个性。
她怕是以为她那位表哥也是吃素的了,主意都打到了他的头上。
稚陵并不完全明白这位差官怎么突然看着她的目光带有浓浓的同情,仿佛她即将遭遇什么大厄,但她不及深思,觅秀已连拖带拽地把她给拽进了门。
礼光殿外殿尚有官员筹备,正殿才是真正饮宴之所。她打量着礼光殿内内外外,雕梁画栋,团凤游螭,碧瓦飞甍,钩心斗角,莫不精致轩丽,贵气横生。
稚陵还在神游天外,想着这一块砖瓦得多少银子,能买多少根糖葫芦,觅秀都快把她胳膊摇断了:“姑娘!姑娘快去呀!”
显然觅秀是一眼瞧见不知哪里走出来的董大夫了。董大夫从游廊过来,还在跟边上一位大人严肃地说着什么,一张国字脸快要皱成圆脸了。
伸头一刀缩头一刀,终得过去,稚陵如是想。
她从容步到董大人跟前,行了一礼,不卑不亢地道:“大人,裴稚陵许久不见宫里人的安排,擅自寻了来,还望大人不要见怪……只是裴稚陵不知大人究竟的安排是……?”
她也不知自己心底有没有想要董大人给她做主,也许那样董大人就要得罪了薄大小姐。但若说什么没有一丝期盼的,也不能够问心无愧,谁私心里又不期望得一点偏心呢?
她无意识地绞着手指,落在觅秀的眼睛里,姑娘那是不自信的表现,觅秀拉了拉她的手,示意她不必太紧张。
她微微咬着下唇。余光扫着四周,却忽然瞥见一道绯红的身影沿着游廊直往她这边气势汹汹地行来。
气势汹汹,她想,这词的确合适,那位姑娘的衣裙翻飞得厉害,几乎要翻成一朵鲜艳夺目且正盛放的芍药。
董大人大抵没料到她能寻到礼光殿外殿来,先是诧异了一下,随后低叹:“此事到底是老夫虑事不周,对不住裴姑娘了。薄大小姐已在名册上添了名字,”他捋了一把胡子,偏了头,续道:“裴姑娘若是要回谧园去,老夫命人替裴姑娘备车马。”
觅秀使劲给她使眼色,她撅撅嘴,隐匿了心中一分不情愿地继续开口:“可大人先前已在案中录下裴稚陵的名字,如今临时改替,大人这番作为,若是陛下知晓了……?”
聪明人会将话留一半,好让旁人继续遐思去,而她话留一半,着实是因为她并不知陛下若知晓了究竟会怎么办。但她揣度一定是极难熬的处罚,八万遍论语可见一斑。
这时候骤闻一道娇莺般的声音响起,稚陵抬起眼,正好与那位芍药花似的姑娘四目相对。
“哦,欺君?董大夫方才原是在愁这个?这很好办,董大夫替裴姑娘报一个断了腿脚上去,由我薄云钿顶替上就是了。”
稚陵只见这位姑娘梳着朝仙髻,簪了一枝艳朱色的花,生得眉目浓丽,一双眼的眼角仿佛带了钩子。唇色红得欲滴,她觉得唯有春夏季里成熟的樱桃可以与之一较高下了。
她今日着的是袭朱裙,是为显喜庆,而薄云钿也是袭红裙,似比之她的裙子要红得更深浓些,衣裙上掺金线绣有细微花纹,她微微抬袖,那些花纹便折射起光来,晃人眼睛。
她想,这位薄大小姐就算不是大小姐,也可以靠脸吃饭。
薄大小姐却并非是在说什么玩笑话,她虽脸上含着几分笑意,但那只令人看得心慌。
“可咱们姑娘又没有伤了手脚,大小姐今日这般,难道不怕……不怕欺君么?”觅秀扬起头,把稚陵给拉到了她身后护着,直视薄云钿。
薄云钿扬了扬眉:“你怎么晓得本小姐欺君?你们姑娘若是真的伤了手脚,可不就不算欺君了?”她声音宛转,一字一字余韵留长,却教在场的人纷纷胆寒起来。
这话是什么意思简直再明白不过了。
稚陵一行几人全愣怔住。即墨浔怎么醒了,还追过来了。她想,倘若他清醒了,便晓得刚刚让她留下是极不妥的做法,他的个性不会为她坏了规矩,所以她就算半夜悄悄走了,他也不会太过生气。
未等稚陵开口,即墨浔两三步踏过来,却是再次拦腰抱起她,一路却走得极缓,月光如银练,洋洋洒洒泻落,他轻声说:“两年前是两年前,今时不同往日,……”
稚陵怔在他的怀抱中,这怀抱温暖结实,仰面正是皎皎的月亮。
“今时往日,……”她敛下眸子,声音很轻,她心中想,还有什么不同的么?
夜里蛩声此起彼伏,吱哇吱哇吵个不停。薄薄的酒气,浓烈的龙涎香味,纠缠得不分彼此,铺天盖地。他的嗓音缓缓响起:“今时今日,我好像……不能没有你。”
第42章第42章
仲夏夜里,月色如银,步伐缓缓,偶有几只绿萤火虫,忽明忽灭的,闪过眼前来。
即墨浔低眸注视着怀中人,醉意上头,他不由得想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往事,日久蒙尘的秘密,……他愈发觉得世界上不能没有稚陵了。或许不能叫整个世界——但至少他的世界,已全然与她有关。
这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相遇相逢,然而都飞花落叶一样过去,……但她只是一叶浮萍,依傍他而生,不会离去。
不会离去。
他大约是真的喝多了,连素来收敛的笑意,挂在嘴角,弧度却愈扬愈高,到最后竟低笑出声。
稚陵哪晓得他想到什么,只觉原本缓缓的步伐骤然加快,待跨过涵元殿高高的门槛,一路三步并两步地进到他寝殿里,他紧抱住她,双双倒在了沉香木龙榻上。
蟹黄酥吃得很快,她手指戳了戳油纸,没有摸到下一块,才颇为遗憾地唉声叹气了一番,心想着贵的东西总是用得这样快,琳琅馆的胭脂是这样,碧月阁的漆金墨是这样,四明坊的蟹黄酥也是这样。
她把四明坊出品的精致油纸对折再对折,折成边边角角对齐的小小方块以后,才丢进了屋子里的纸篓。
这流云榭、抱棠苑、澄熙堂三点一线的生活她过得还算是很快活的,也乐于这样的循规蹈矩,何况在这里偶尔还可以大方一把,享受烧一烧钱的快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