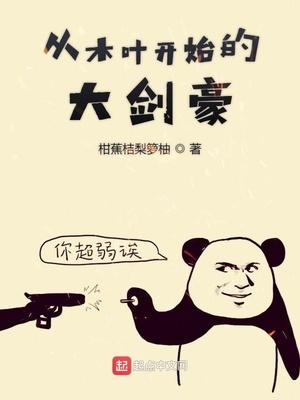52格格党>觉醒年代同人-延然薄暮 > 误会(第2页)
误会(第2页)
后来,乔年迷糊起床上厕所,却看见这样的一幕:
“。。。压迫者和被压迫者,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。。。”
“停!从‘但是,我们的时代,资产阶级时代’那里开始。”
“但是,我们的时代,资产阶级时代,却有一个特点: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。。。”
。。。。。。
乔年看着林诗然和陈延年“和谐”的一幕,连瞌睡都没有了。
他想起了小时候背课文,哥哥也是这样,认真严肃地监督他背书。他时常想象哥哥背书是个什么样的~
今儿算是见识了,原来哥哥也有今天啊~~
乔年肉嘟嘟的小脸上露出一个可爱的笑容。
经过了林诗然用了大半夜时间的努力,终于从陈延年口中得到一句“确实值得探索”。
虽然这不代表他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,但是有那么一丢丢的苗头了。林诗然已经觉得倍感欣慰。
接下来的一周,日子虽然照常过,但是互助社的各项生意越来越惨淡,而且还有少许人开始陆续退社,更重要的是,大家根本就没法做到绝对的共产,首当其冲的就是家庭,父母总归是想要和子女们吃顿饭的吧,好久不见肯定要吃顿好的吧,下馆子不过分吧?所以,同吃也慢慢地变成了一个问题,因为种种无法让人拒绝的理由,今儿这个不在,明儿那个不在。
虽然北京的冬天很是寒冷,但阳光还是带来了些许暖意。这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。
白兰在房间里算账,互助社的资金已经越来越少,她重重叹了口气,不觉心急如焚。
“白兰姐,怎么了?在门外就听见你叹气了。”林诗然扭了扭脖子,从门外走了进来,她本是想来小憩一会,下午好回家帮着赵纫兰做做家务什么的,反正互助社的事务也不是很多。
白兰转过头来看着林诗然,随即又朝着门口探了探头,见没有其他人,压低了声音说道:“不瞒你说,社里的资金有些困难。你可别告诉其他人,免得大家担心,其实也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”
林诗然坐在铺位上,听得白兰的话,想起那日教室里陈延年坚定的神情,她沉思了一会,问道:“白兰姐,你们那个学校有想学钢琴的女孩吗?”
“钢琴?”白兰冷不防被林诗然的问题弄得有些懵,“倒是有一个,那小女孩家庭条件不错,听说她的妈妈好像正在给她找一个钢琴老师。”
“你觉得我怎么样?”林诗然双手撑着铺位,笑盈盈地看着白兰。
“你?然然你的意思是。。。。。。”白兰忽然反应了过来,这丫头是想补贴互助社吗?
“我可没什么意思啊,”林诗然打断了白兰的话,大眼睛轻轻一滑溜,“咱们社走到今日不容易,虽然不是什么长久之计,但是先撑着吧。这事你可别告诉其他人啊,我可不想当好人。”
白兰想,这丫头嘴硬得倒挺像陈延年。
大钊先生今日下午难得闲暇,把稿子写完了之后,便往家里走,路上在买星华与葆华最爱吃的糖葫芦时,想起林诗然下午要回家,不由得多买了一串,在他看来,林诗然不过才十六岁,也还是个孩子。
回到家时,看到赵纫兰正费力地劈柴,她前额的碎发散落下来,额头上布满了细汗。大钊先生急忙放下了手中的公文包和糖葫芦,不由分说地拿过了赵纫兰手上的斧子,心疼地说道:“姐,不都说了,以后这些活儿等我回来做。”
赵纫兰看着自家丈夫心疼的模样,用手利落地将碎发别在耳后,笑了笑说道:“不妨事不妨事,你最近不是很忙嘛,以前你不在,又不是没做过。”
大钊先生的目光不经意间投向了妻子的手上的伤口,他眉头一皱,将赵纫兰的手拿了起来,妻子的手略显粗糙,是这个家为她留下的印记,他轻轻抚了抚:“姐,怎么受伤了也不知包扎?”语气表面上透着几分责备。
“嗐,一忙起来就忘了,也不是什么大事。”赵纫兰站起身来,充满爱意的眼神毫不避讳地投向大钊先生。
“姐,你等会。”大钊先生便要进里屋去拿包扎的东西,顺带着冲另外个屋叫道,“星华,葆华,出来吃糖葫芦啦。”
星华、葆华闻声而至。赵纫兰看着两个孩子兴奋的身影,不忘嘱咐道:“不能贪多啊。留一串给你们然然姐姐啊~”
林诗然回来的时候,刚好碰见大钊先生和赵纫兰相向坐在院子里,大钊先生正捧着赵纫兰的手仔细地包扎着,时不时地还在吹气,生怕把妻子弄疼了似的。赵纫兰望着丈夫,眼里是满满的情意。
阳光斜照,穿过院子的屋顶,恰好投射在二人的身上,那份岁月静好让将这一切尽收眼底的林诗然感慨万千。
她双□□叉地倚在门框上,歪了歪头,仿佛是已经醉在这个场景里了。
真好。这样相濡以沫的爱情可真令人羡慕。
其他人她不知道,陈延年那家伙是绝对不会做出这样举动的!
林诗然打了个寒颤。
咦。。。怎么会突然想到这家伙?关他什么事!
林诗然将手背在身后,学着戏里的官员迈着方步走进了院子,又学着古时的老学究们转着小脑袋说道:“执子之手,与子共著;执子之手,与子同眠;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;执子之手,夫复何求!”说完最后一个字,林诗然刚好就站在了自家舅舅的身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