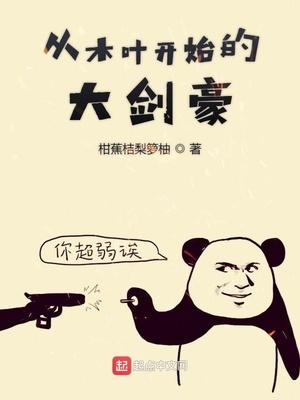52格格党>末周父母 > 第 1 章(第7页)
第 1 章(第7页)
三爷爷比爷爷小三岁,太爷爷的兄弟们和他们的儿子因为种种原因相继死去,等三爷爷刚长到二十岁,李家一脉就只剩三爷跟爷爷。
三爷爷不知到底姓什么——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奶奶总是私下里偷偷告诉我说,不是一个姓的人,住在一起多久都终归不是一心的,于是我才渐渐知道,他不是我的亲爷爷。
三爷爷四岁来到李家,正是腊冬时节。太爷爷早起天地都是一片雪白,一丝声音也无,他正要去地里看庄稼,走到北边地里,却发现破败的人家院门旁蜷缩着一个小小的人,衣衫褴褛,他就问那孩子,怎么冰天雪地的不回家去,那孩子只有一口气,睁开眼看看他,张嘴就是异乡口音,可嘴里却含糊说不清楚。再往北就是集市,于是他抱着这个瘦干的孩子回家,后问遍乡邻商贩,无人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家的。
太爷爷决定留下这个孩子,起初太奶奶埋怨他,不过终究是个男的,养大了就能种地养家的。
三爷刚来李家,躺在床上烧了十多天,嘴里说着话,但无人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,于是大家都说他是南边的人,猜想许是这孩子生了病,没钱给看,才扔了的。他却听得懂我们说的,叫他吃饭洗脸洗脚,他样样都听得懂,太爷爷请来邻村的宋伯,他开了药,说,只怕烧退了,这孩子也要落下残疾的。
有了药方,却抓不起药。于是,太爷爷上山给三爷挖药,有时一个山头只能挖到一种药,于是太爷爷跑遍方圆的小山,一样一样的挖。
那个宋伯果然是个能看病的,太奶奶说,三爷爷样子不丑,只是他刚一下床,太爷爷就发现他有点跛。
太爷爷说,瘸就瘸一点吧,能说能听,脑子也不傻,照样利索。
姑奶奶比爷爷大七岁,三爷就跟着姑奶奶烧饭,洒扫,给地里干活的大人送饭,等到姑奶奶出嫁,烧火做饭放牛的差事就变成了他的,直到他进学,奶奶嫁了过来,虽然不用再烧火做饭,却依然放牛。
三爷长到七八岁,他也慢慢学会了我们这里的腔调,人们都慢慢地听得懂他说话了,只是有外归的生意人说他有闽地的蛮腔。
他那时已经牵着牛跟村里的孩子们到处放牛,却始终不大言语,因为带头的大孩子总笑他是没人要的蛮子,其他的孩子也跟着哄笑说他是个瘸子。
三爷是个闷葫芦,别人说他什么,他也不言语,他心里有气,也不说。
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脾气,我只知道,每逢有集,他总要带上我,他爱吃糖糕,所以总问我吃不吃。
我还随他趟过河去淮河南岸的集市卖菜,河水并不很深,河水清亮亮的,我执意要自己趟过去,可他每回都把我驼在肩上。
他一瘸一拐地走,我也就上下左右地晃,头顶上的太阳越升越高,身下的河水就越发地透亮,远处的河面更像洒满碎银,又像天晴的夏日里满天的星星,真是漂亮,就像置身天上瑶池一般了。
我爹不许我跟哥哥们一起读书,他总说,小妮子认得几个字不当睁眼瞎就不错了,他板起脸训斥我的样子,跟爷爷一模一样,让我心生畏惧。
在我爹面前,三爷说不了什么,他当不了我爷的主,如今也当不了我爹的主,可他总有办法给我弄来书塾里书生的诗书,教我写字念诗。
书塾的先生是三爷的好友,先生曾对我说,他们少年时在一起读书,三爷是作诗最好的那个,只是因为我家家贫,三爷才没去考取功名。
与我同岁的女孩子,都要帮家里做事,洗衣做饭织布裁衣。这些有何难的,天天做来也实在无趣得很,我也讨厌总被兄弟们指派。
娘始终想让我读书,舅舅们也说让我读书,可是我爹不愿意,他说,女人读太多书没什么用。
兄弟们上学堂,路远不便。天降雨雪,我就走上三里路送饭去。先生的院落还不比我家的大,书房却有三间,人一进去当真书香四溢。
不仅如此,那先生院内院外满植梅花,我跟三爷说起,三爷却笑,读书人就是淡泊高雅。
我娘总是在我跟弟妹跟前抱怨爷爷奶奶如何不讲良心,苛责为难她,又例数我爹如何懒惰,自私精明,她还说我是白眼狼,叫我不要跟三爷爷太过亲热,她说三爷爷是外人。
娘说的,我不是很明白。先生吩咐温读的诗书,我也不甚明白。给哥哥们送饭时,我喜欢趁这个空当儿看先生摇头晃脑的诵读,我喜欢先生身上那一派书生意气,也喜欢他的可爱儒雅。
家中的事情我虽然不懂,可是听到奶奶对娘的埋怨,娘背地里对爷爷奶奶的数落,我总是回避这些争执。
去往先生家的路,春天有桑树,桑树结桑葚,桑葚进了孩子的嘴,染红他们的唇舌,桑叶则被农妇采回喂蚕;榆钱嫰绿时凉拌可食;仲春有随处可见的白茅根,小孩儿在幼嫩时掐它来吃,入嘴甘甜,倘若长老一些,便苦涩难咽。尽管如此,冬天结束,地气一动,天渐渐暖和,每年这个时候我的嗓子就肿痛难忍,后来也就渐渐知道,虽然白茅遍地都是,不大起眼,却是清热利尿解毒的好药。
天最热的时候,小路两旁浓绿成荫,知了一气地聒噪,倘若夜里坐在门口,凉风带来稻田里的阵阵清香,混合着水汽,牛蛙嘹亮地叫着。
我很怕冷,不喜秋天和冬天。冬日里奶奶放在雪窝里捂着的冻豆腐,一经冰雪冷冻现出许多气泡,配上腊肉在瓦罐里咕嘟嘟地熬着,奶奶冻得嘶嘶地直吸凉气,而我探着脑袋,伸长脖子去看瓦罐里咕嘟咕嘟翻滚的热汤,热气直扑到我脸上,豆腐上黑洞洞的气泡里灌满汤汁,咬下去软嫩而多汁,汤非常烫,烫的我的喉舌发痛,但因为这点温暖的香气,我才不那么厌恶冬天。
腊月里下最大的雪时,别的私塾早停课了,可我的两个堂哥依然要摸黑起来上学。他们出门往西走经过我的窗下,偶尔我被他们的说话声吵醒,睁眼一看,觉得窗外很是明亮,扭头看窗外时,就知道此刻的白不是天色的白,而是雪色。
未进书塾前娘也教我念诗,可我全然没有心思,总也记不住,娘总斥责我,也常常罚站墙角,不许出去玩。可妹妹总能摇头晃脑地记住,于是人前人后地直夸妹妹比我聪明,我很沮丧,更加没有心思读书,可是邻居孙大娘见我写字总夸我写得一手好字,将来是能做女先生的,这时候我就很高兴。
乡下的教书先生少,女先生则少之又少,人都说物以稀为贵,一想到往后能做个贵人,我就更高兴。
因为这点巨大的憧憬和喜悦,我就立了志,要好好读书,比哥哥们读的更好,就算不能科考,那也要做个教书的先生。
可哥哥们听到了,总说我是黑丫头,黑黢黢的一个丫头,竟然还要当先生。
我气不过,跑去问三爷,三爷却给我打气,我又去问娘,娘不发一言。
女子发奋读书,难道是错的吗。
我也怕三爷,却不是像怕我爷那样子怕。自从知道我立下当女先生的志,背诗磕巴了,三爷就打手心,我念书懈怠了,他也打手心。
我被打的痛极,倒吸凉气,不住的缩手,三爷却扯过我的手继续打。一边打,一边说,“你的天资不如你小妹,你娘因此夸赞小妹,你就应该更加争气,否则,你的兄弟们就会取笑你,盈儿,记住了吗?”
我写的字,写的文章,他都夸我写得好,夸我比哥哥们写得好,拿去给学堂里的先生,先生也夸我写得好。